今天我们要说的作品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·雨果的代表作《悲惨世界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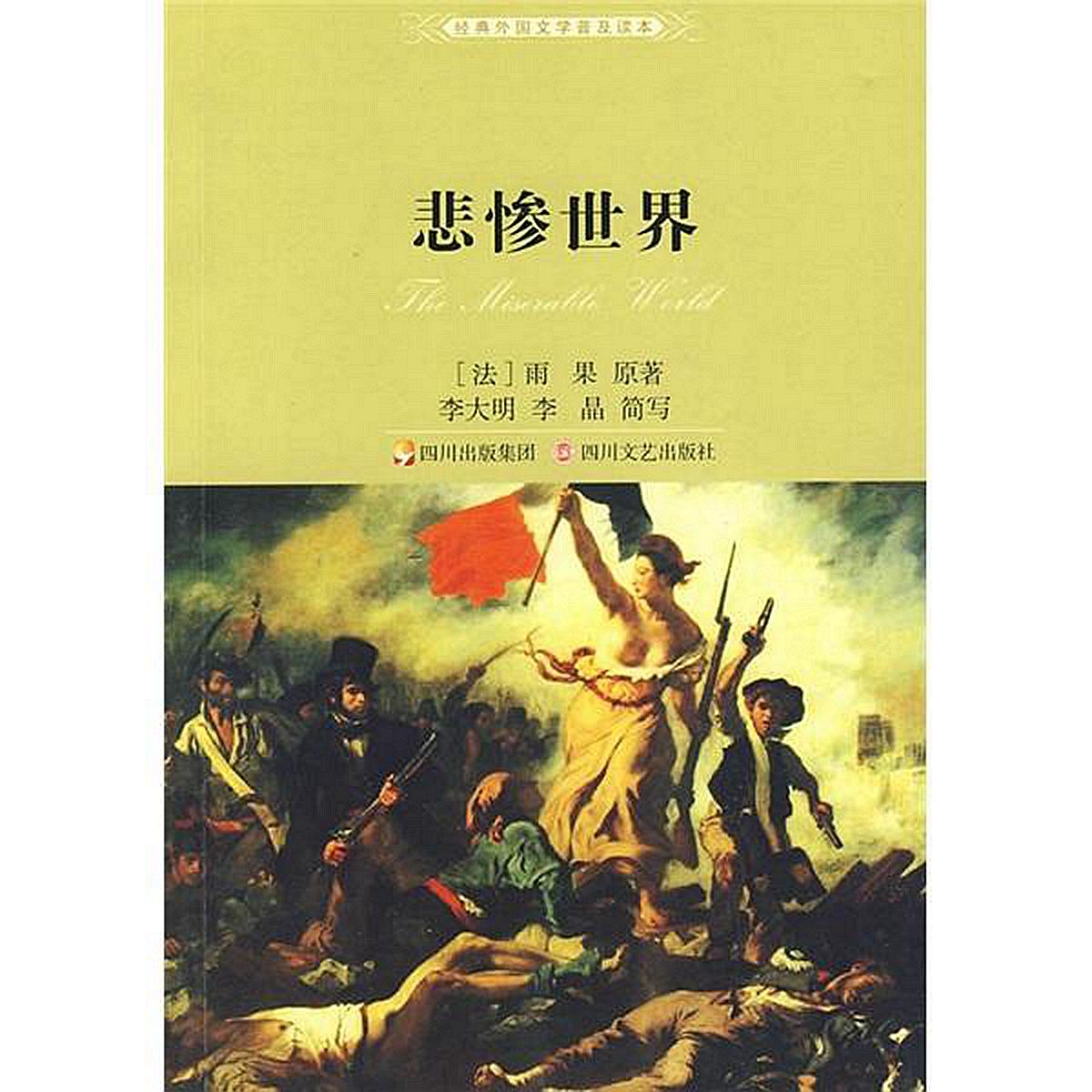
跟《巴黎圣母院》比起来,《悲惨世界》的篇幅更长,世界观也更复杂。如果说写《巴黎圣母院》时候的雨果,还在努力讲好一个故事,那么到了写《悲惨世界》时,他就隐约扮演起了造物主的角色。所谓的“造物主”,是说他不仅要给我们人物与故事,还要给我们整个世界。这个世界不是对现实的照抄,也不是对历史的还原,它比现实更鲜活,比历史更深刻。读完这部《悲惨世界》,你可能仍然不清楚19世纪上半叶法国发生过几次革命,诞生过几个共和国,建立过几个王朝,有过几个帝国。不过,你大概率能感受到善的力量,正义的限度,自由的可贵,道德良知的价值。

《悲惨世界》写作的历史背景主要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32年巴黎起义这段时期。早在19世纪40年代,雨果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。起因是他听到这么一个故事,说有一个苦役犯出狱以后,人们排斥他。当他走投无路时,一位善良的主教帮助了他。在主教感化下,苦役犯从此改过自新,加入了主教弟弟的军队,一路英勇作战,直到在滑铁卢战死沙场。

在雨果最初的计划里,除了主教和苦役犯,他还打算写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。当时法国文坛的潮流之一是描写民众的痛苦,雨果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建树。据学者研究,法国大革命的初衷是对自由的追求,这种自由更多是政治上的,主要是那些有钱没权的阶层想要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,因而反对教会和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。后来,底层民众才进入了革命者的视野,公平逐渐成为革命主要的诉求。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,作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底层的无产者。雨果在小说中塑造苦役犯和女人等人物的初衷就与这种思潮有关。

但雨果对大革命的态度比较复杂。虽然他支持法国大革命对自由的追求,同情民众的遭遇和苦难,但对革命之后越来越极端的举措持保留态度。所以,我们会看到雨果笔下的人物往往善恶分明,可是他对革命、历史、宗教的态度却十分暧昧。说到底,雨果并不是某一种政治体制的支持者,他更看重自由、平等和尊严,强调人性的健全和良知的完整。所以说,人们往往把他称为“人道主义者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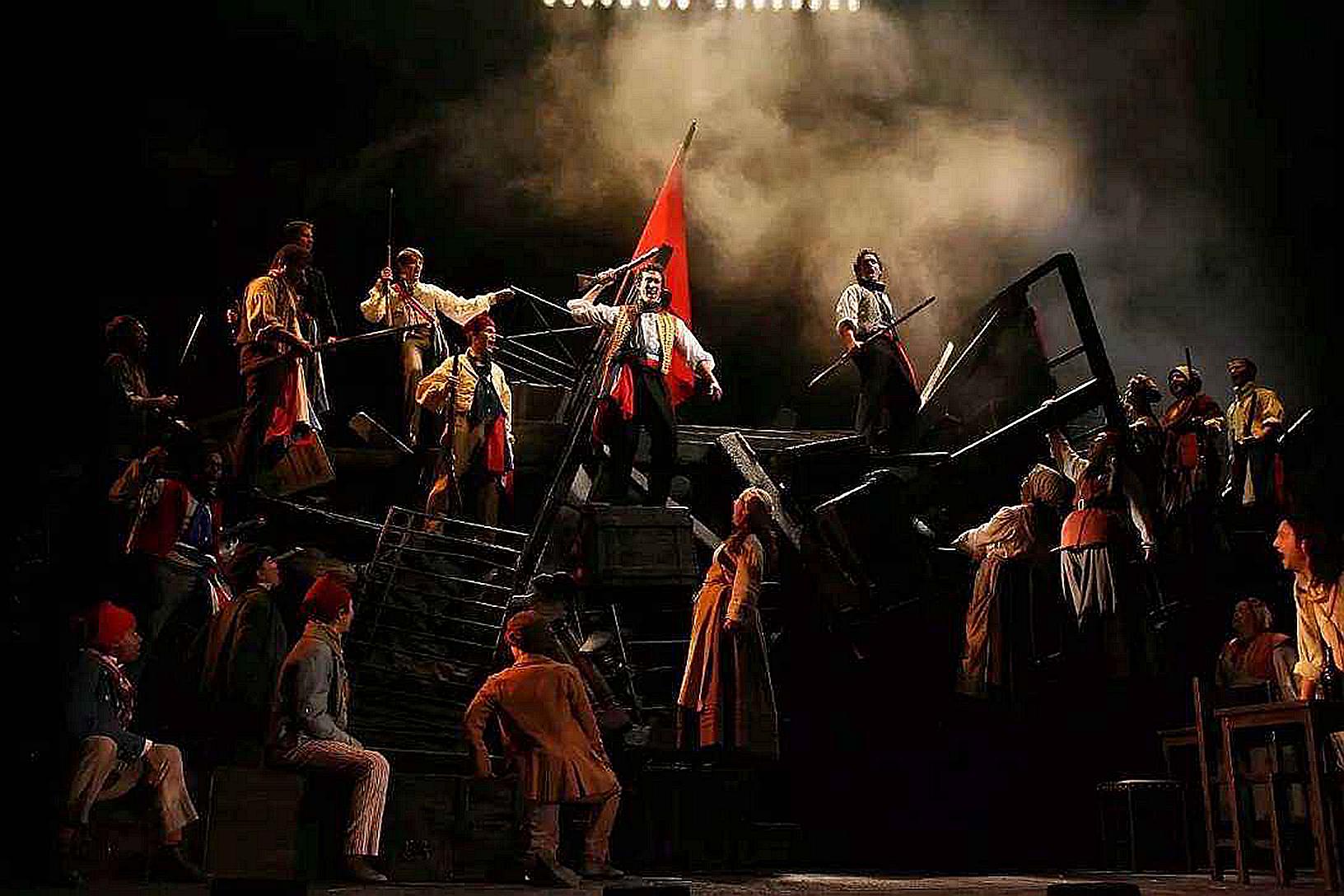
《悲惨世界》的写作过程并不顺利。雨果在40年代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,当时的法国施行君主立宪制,社会相对稳定。但这种稳定没能持续多久,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,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,拿破仑的侄子路易·波拿巴当选总统。在这段时间里,雨果中断了写作,四处奔走鼓吹革命,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,晋封伯爵,并当选国民代表和国会议员。

1851年,路易·波拿巴称帝,雨果对此大加攻击,被迫流亡比利时。直到1861年6月,小说才全部完成,第二年正式出版。全书共分为五部,翻译成中文有90多万字。除了最初计划中的圣人、苦役犯、女人和孩子,雨果还塑造了马里于斯,一个带着不少他本人印记的年轻人。至于小说的主题,雨果自己归纳为:一个人良心的发现。

整部小说采用框架式的结构,每一卷、每一部似乎都在讲不同的故事,相互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,有时还夹杂了大段雨果的议论和抒情。这一点曾被当时不少评论者批评过。不过,巨大的篇幅抚平了作者议论和抒情引起的突兀感,松散的故事最终都汇聚在同一个主题之下,所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止是几个人物、几段故事,而是整个波澜壮阔的世界。
